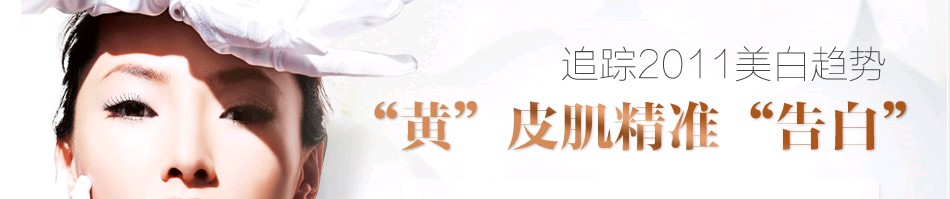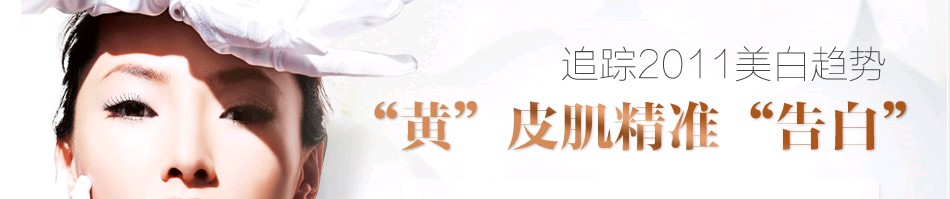| 长江商报消息湖北武汉是辛亥革命的故乡。因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的缘故,一些纪念性的文学作品涌现,因而有评论家称:“关于辛亥革命的写作渐渐成为湖北文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于作家来说,此类作品调集了他们对生养自己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了对它的认知和自豪。 湖北作家眼里的“武汉人与辛亥革命,女性情感,同为湖北文学界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献礼作品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武汉首义家》,日前在武汉首发。这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作家望见蓉、牛维佳创作。 武汉作协签约女作家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取材武昌起义大量亲历者回忆录,记录了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以汉口英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两代人在武昌起义血与火、家与国的恩怨情仇悲观离合的生活故事为历史背景,以武昌起义酝酿发展爆发的史实经过为线索,展现武昌起义从花园山聚会,到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到军队同盟会,到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和共进会,两股力量最终合流,打响武昌起义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一组起义英雄的光辉群象。 望见蓉告诉记者:“我要让男性读者从中读到修旧如旧的武昌起义史,又让女性读者读到她们牵肠挂肚荡气回肠的爱情”。她把这部小说的基调定位为四个字——“铁血柔情”,即革命加爱情,战争加生活。这样,小说书写的战争是生动的历史背景下的历史真实再现,描写的爱情也是时代和社会倒映在人们生活中的情感折射。 省作协专业作家牛维佳的《武汉首义家》则主要讲述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汉一民族资本家顺应反清大势和主张的政治需求,他参加抗击清军,经历二次革命,并随着帝制的破灭和“”的产生,发生一波三折的转变。 女性情感“说到武昌起义,毫无疑问左右民心民意的,是民生的取向,民生则是由生存所必须的种种条件所决定的。”用牛维佳的话说,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就是从民间的视角,去描写在这一背景下的普通武汉人,和他们想的与做的。由辛亥革命而产生的武汉民间的变化,才是这部作品描述的主旨。 他说,自己在作品中不但描写了许多市民纷纷斩木为兵抗击清军,和商民们出钱出力的一面,也描写了武汉市民民风强蛮的常态,从这些常态中,展现那场革命的民众性和真实性。这些渐行渐远的往事早就硝烟散尽,当我们今天说到它的时候也许谈论更多的还是革命党,而鲜少提及那些做出过牺牲的普通武汉市民。但是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忘掉他们的。 ◇点评 方方:所有的革命都是人的演绎 省作协主席方方特地在首发式上祝贺两位作家,并发表自己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感言。在她看来,所有的革命都是人演绎的,而文学就是人学,正像望见蓉、牛维佳写作《铁血首义路》、《武汉首义家》那样,人在革命中的经历和情感会由作家予以记录。两部作品都反映了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革命的支撑以及他们的命运。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回首那段历史,有三点让方方感到印象深刻且颇有感慨。首先是早期革命者的情怀。他们希望让汉人重登历史舞台以改变中国、改变人民命运的纯洁想法,加上每次战事中都冲锋在前、全然不为个人利益,以及完成任务后自动退出的这种精神,在政治上说是幼稚,但从个人来讲,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情怀。 其次是湖北人的务实精神。由于身处内陆,武汉的革命者相比上海等地活跃的政治人物来说比较土俗。但正是这群“土包子”当年能放下身段,参与到军队中,暗中运作,把军队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使得整个湖北新军多半都是革命军,导致最后革命能取得胜利。再次是民心。起义之后全城百姓倒戈,都参与到革命中去了。清军之所以很快被灭,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 本报记者卢欢 |